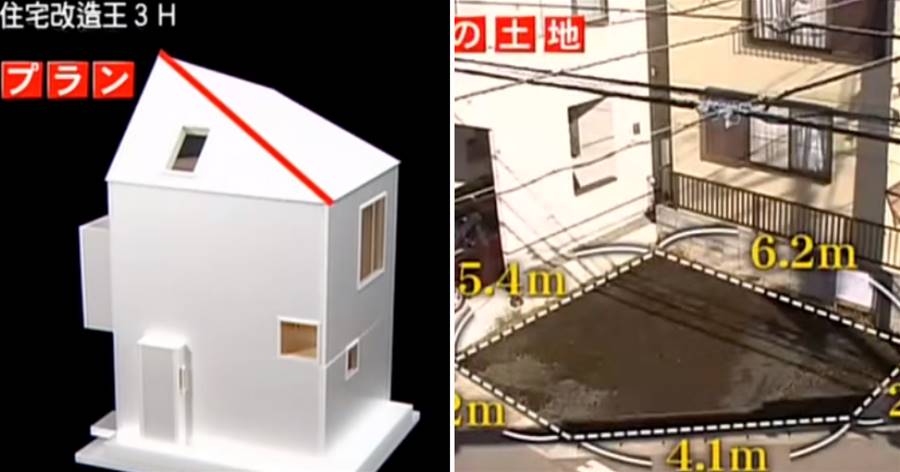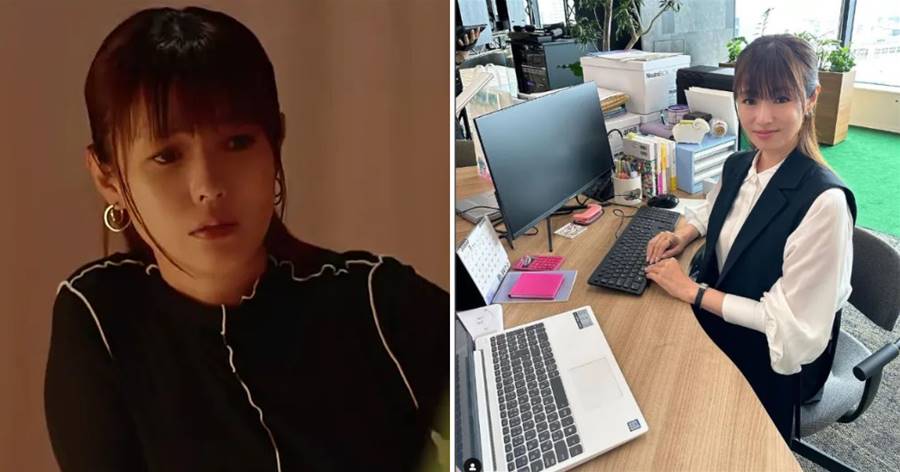小說家看電影的時候,腦子裡想的東西和我們一樣嗎?同為故事的編織者,他們會不會更明白編劇和導演腦中的溝壑?
歡迎收看「小說家看電影」欄目,和我們一起閱讀內行們的看片思路。
炎炎夏日,最適合去驚悚片裡體驗刺骨涼風,而《閃靈》被稱為恐怖片之最,被大雪封鎖的山頂酒店最「清涼」不過了。就讓小說家帶我們重新開啟這段恐怖之旅吧!
✎
003

讓恐怖的故事永遠佩戴著寫實的徽章
私下裡,我對電影的區分大概有三類,分別是「看不下去的」、「看一遍就行了的」和「需要看好多遍的」,所以突然提到「類型片」這個分類概念,就有些似懂非懂。印象中,類型電影的特點應該是相對模式化、擁有固定的套路、類似流水線上的工業產品。但是即便如此定義類型片,也不能抹殺該類電影同樣是創意作品的本質,好的類型片總能在固有的套路下玩出新的花樣。
借著這個話題,我終於有機會談談一直以來都令自己著迷的一支驚悚片派系。這個派系的片子相對小眾,不過吊詭的是,其麾下的影片數量卻一直在穩定增長,每隔幾年都會出來那麼一兩部,讓人大過眼癮。
聊到這個派系,姑且拿斯坦利·庫布裡克的《閃靈》來做一些並不專業的個人隨想。

斯坦利·庫布裡克
在電影《閃靈》的故事裡,貌似和諧的三口之家在一座大雪封閉的山頂酒店做看守,男主人傑克本想利用這段封閉的時間完成自己的創作,不料漫長的隔絕和孤寂讓他逐漸失去理智,在家庭瑣事的困擾中變得狂躁易怒,而終於催生了一場驚悚的兇殺案。
《閃靈》裡的心理分析學
讓一個原本儒雅的人淪為殺親者是極難做到的——為此,故事賦予了傑克一個封閉的環境(大雪封山後的眺望酒店),和獨特的個人困境(創作焦慮、因誤傷兒子而自責、戒酒以自我救贖),以此作為背景,用巧妙、連貫的幾件小事一點點逼瘋了這個身為作家、還教過書的文明人,讓他舉起與自己身份極不相稱的斧頭,從而使邏輯上看起來有些費解的兇殺案變得可能。

不管是影視作品還是小說,我都對故事裡人物的變化饒有興致,尤其是那種兩極反差的顛覆性變化。在《閃靈》的故事裡,傑克精神弧線的發展自然、完整、有說服力,劃分起來大致有三個階段——
第一階段,壓抑和掙扎:在酒店面試的場景中,傑克·尼克爾森的表演可謂精湛,他細微的言行舉止準確地傳遞著故事所需要的資訊——面試過程中,刻意偽裝的自信裡流露出這個男人對「酒店看守」職位這根救命稻草的重視,也從側面暴露了在無業家庭中,作為失業丈夫這個角色的巨大的精神壓力。接下來,一家人搬進酒店,短暫的新鮮和歡愉過後,面對打字機上空白的稿紙,傑克只能在酒店大廳拋擲網球緩解焦慮——他在掙扎著,企圖讓一切回到預設的正軌之上。

第二階段,憤恨和放棄:當傑克終於捕捉到寫作靈感,卻在創作時被突然闖入的妻子打斷,兩人的對話漸漸升級,氣急敗壞的傑克完成了從焦慮到憤恨的過渡。衝突來得太快,往往會削弱故事的可信度,緊接著,影片安排了一場殺妻的噩夢,這讓驚醒後的傑克陷入恐懼和自責,恢復了對妻子的溫情。
在這個節骨眼上,兒子受傷了,妻子對丈夫行兇的妄加揣測,撕開了折磨傑克多日的舊傷。往日誤傷兒子的指責撲面而來,救贖變得不再可能,他終於開始自暴自棄——甚至願意用靈魂來換一小杯波本威士卡。

第三階段,釋放和毀滅:幻想中的酒吧和波本威士卡,237 號房的裸體女人,這兩個恐怖、詭異的元素代表著「家庭禁錮」中男主人壓抑的欲望。在這個階段,傑克身上的社會文明迅速消退,他開始釋放本能的欲望,如果有一杯威士卡,他願意放棄戒酒;如果有一個女人,他願意背叛妻子。對家庭的反抗在最後的爭執中爆發,妻子罔顧傑克的工作使命,執意帶兒子離開酒店,爭執之下,她對傑克進行了防衛性的攻擊,使對方徹底釋放了毀滅的野獸。

237 號房
在電影《閃靈》誕生的四年前,波蘭斯基的電影《怪房客》同樣譜寫了類似的兩極顛倒的心理弧線發展過程,相對於「對家庭對反抗」,波蘭斯基所思考的則是「對身份認同焦慮的反抗」。
相對於《閃靈》,《怪房客》裡誘導主角發生精神轉變的激勵事件略顯刻意,因此造成主角的變化顯得突兀,讓人看來費解——或許是因為《怪房客》裡的主角本身就具有性格缺陷,所以人們在觀影時並不能做到很好的情緒帶入。

《怪房客》海報
把「原罪」的恐怖具象化
很難找到一個詞彙能夠把「家庭的禁錮」「信仰的混亂」「欲望和恐懼」「身份認同的焦慮」……之類負面的概念全部囊括,所以我選擇把它們統一而粗暴地理解為「原罪」的不同形態。想要在影片中把這些「原罪」的變量具像化,那麼恐怖元素無疑是最符合其氣質的。
在《閃靈》的第三階段,幾乎所有人的「原罪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具像化:237 房裡的裸女具像化了傑克對妻子的厭倦,脖頸上的傷口具像化了兒子丹尼對 237 房的恐懼,喧鬧的大廳和憑空出現的酒保具像化了傑克飲酒和傾訴的欲望……
庫布裡克在對原罪做具像化處理時,主要選擇以劇中人看到幻覺的方式來體現。如前文所舉的幾個例子,在某種焦慮或恐懼的境遇下,所有人多多少少都產生了一些特定的幻覺,這些幻覺是輔助性的——它們成功增強了影片情節的驚悚效果。
而在羅伯特·艾格斯的電影《女巫》裡,同樣的手法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運用。

《女巫》劇照
《女巫》的故事發生在大約處於中世紀末的新英格蘭。密林中意外頻發,虔誠的清教徒一家在「女巫恐懼」的籠罩之下相互指責(和自責),最終走向毀滅。影片中,嬰兒的消失具像化了大女兒對瑣事勞作的厭倦,林中的蘋果和女人具像化了大兒子對食色的欲望,孩子和銀盃的失而復得具像化了母親對「失去」的無法釋懷……不難看出,在《女巫》的故事裡,除了母親的部分屬於幻覺,其它原罪的具像化大多是以事件的形式體現的——它們是讓故事得以發展的拐點,也是影片各個支線故事的結局。
在羅泓軫的電影《哭聲》裡,對原罪具像化的運用則更加出神入化。

《哭聲》劇照
電影《哭聲》講述了一宗發生在韓國小鎮的連環發瘋、兇殺案件,為體現信仰的混亂,故事中的案情神秘莫測,最後同樣發展至主角家庭的毀滅。
夜晚的警局裡,員警原本推斷嫌犯發瘋的原因是蘑菇中毒(符合員警的職業信仰),當他剛剛開始輕信有關中邪的謠言(信仰的動搖),窗外突然就出現了一個邪性的身影(具像化)。當他懷疑是日本人在作祟(符合員警的職業信仰),不顧辦案規則,偷偷潛入對方的住宅中尋找線索(信仰的動搖),馬上就找到了女兒的鞋子(具像化)……影片對原罪具像化的處理不漏痕跡,直接和故事融為一體。
「可人可鬼」的模糊地帶
電影《閃靈》的另一個特別之處,在於除了設定了一種叫「閃靈」的特殊能力之外,故事自始至終都沒有肯定「鬼魂」的真實存在。你可以把傑克的失控理解為鬼魂的教唆、甚至印第安人墳墓對白人的詛咒;也可以按照開頭酒店經理的口述,將其理解為封閉環境讓人精神崩潰後的犯罪故事。當兩種可能性相遇、並存——導演拿捏著影片的風格與分寸,不肯剪斷恐怖故事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臍帶,使所有的恐怖元素都顯得真實可信。
與之相似,電影《女巫》的故事也一直秉持著一種「可人可鬼」的狡黠。
影片中人物的困境和結局充滿了神秘氣息,整個故事都籠罩在「女巫恐懼」和「信仰危機」之中,電影圍繞「女巫」這個概念做足了文章,通篇下來,卻又不肯為女巫的存在下一個確切的定論。那些恐怖情節的發生,既可理解為人物崩潰後的幻象,也可理解為「女巫」對這個家庭的詛咒。
就像影片拼錯了的名字——《The VVitch》,其中「Witch」的首寫字母不是「W」,而是兩個僅靠著的「V」,這個錯誤的單詞很像「女巫」,卻終究不是。

類似的形式,還有波蘭斯基的電影《羅斯瑪麗的嬰兒》。這個故事相對簡單:一對夫婦喬遷新居,妻子懷孕後與鄰里和醫生的相處並不融洽,最後在崩潰中產下嬰兒。故事的開端,丈夫在妻子醉酒昏迷後與之發生關係,並弄傷(虐待)了她,影片從這個情節中[插·入]了一段神來之筆——安排妻子做了一場被魔鬼強暴的夢魘,靠著這個巧妙的設計,完成了對故事的模糊化處理,同時鍛造出了硬幣的兩面。

《羅斯瑪麗的嬰兒》劇照
從現實的一面看去,故事可以概括為:一個女人酒後被丈夫強暴,逐漸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,最後遭遇一群瘋狂的邪教徒奪走了自己的嬰兒。
從靈異的一面看去,故事似乎也說得通:一個女人被惡魔臨幸,在惡魔信徒們的監視和簇擁下,產下了惡魔的聖嬰。
——為什麼這些影片都執著於模棱兩可的敘事,讓恐怖的故事永遠佩戴著寫實的徽章?或許從其收穫的效果中能夠找到一些蛛絲馬跡:這種處理方式在放大了驚悚觀感的同時,也使影片散發出一種奇妙的寓言美感,並嘗試著去抵達某種經典。
最後,假使允許我任性地將它們劃歸為同一個派系,那麼這些影片在相似的模式下,無疑都成功地迸發了各自的新鮮與獨特。而用相反的思維看來,或許所有精彩的電影和故事,在化繁歸簡過後,都會歸宗為一種永恆、普遍的形式。